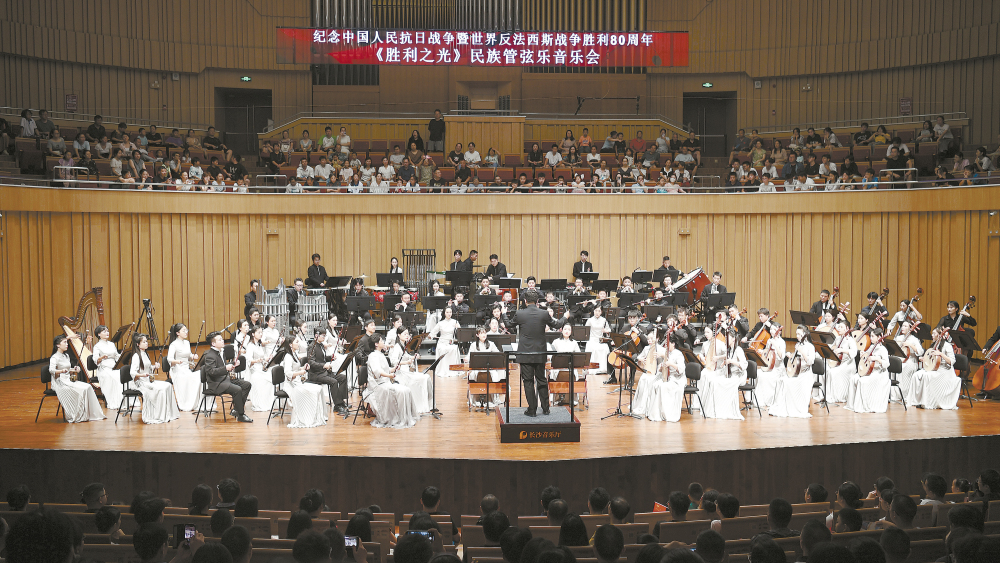張逸云
6月6日,韓少功、李杭育、宗仁發(fā)、謝有順等30多位國內文學名家及研究者,聚集汨羅江畔,重新審視“尋根文學”思想價值、美學成就及對當下文學創(chuàng)作的啟示意義。
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,一場關于文學本質與方向的深刻思索,在中華大地悄然興起。隨著不斷的對外開放,西方現(xiàn)代主義文學思潮涌入,給中國文壇帶來了強烈的沖擊與震撼。面對多元文化的碰撞,許多作家陷入了迷茫與困惑:中國文學該何去何從?
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,“尋根文學”應運而生,杭州召集的一次聚會,成為了尋根文學發(fā)展歷程中極具標志性意義的一幕。韓少功認為,“尋根”思潮的誕生有其必然性:“五四”以來的一百多年,中西文化迎頭相撞,當我們的文化出現(xiàn)越來越多的“他者”對照,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:我們是誰?“我”難道不是“他”嗎?“我”與“他”的界限在哪?1985年,韓少功發(fā)表被視為“尋根”思潮宣言的《文學的“根”》,李杭育發(fā)表了《理一理我們的根》,鄭萬隆發(fā)表了《我們的根》,阿城發(fā)表了《文化制約著人類》……“尋根”對日后中國文學的創(chuàng)新與變革,意義非凡。韓少功的《爸爸爸》《女女女》,賈平凹商州系列的方言寫作,莫言的《紅高粱家族》,阿城的《棋王》《樹王》等經(jīng)典作品,無不從文學的角度探討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歷史和社會現(xiàn)實的關系,試圖尋找中國社會的根源和文化認同。
40年之后,作家們再聚首汨羅江畔,“尋根文學”歷經(jīng)風雨滄桑,早已超越那個特定的文學流派范疇,為現(xiàn)代人提供了一條回歸本真的路徑,實現(xiàn)了對文化記憶的重新發(fā)現(xiàn)。
如今,我們驚異地發(fā)現(xiàn),當下的文學失卻了賴以生長的故土根基。文學似乎遠離了“生活”,地方性敘事日漸式微,被推向了同質的泥潭。
在人工智能崛起的當下,具有強大“深度思考”與“聯(lián)網(wǎng)搜索”功能的AI大模型一再迭代升級,重讀韓少功筆下的“文化之根”,我們不禁思考,當創(chuàng)作過程被技術深度介入,文學的獨特性存在于何處?虛擬空間重構文化根系,這種“數(shù)字尋根”,通過技術手段激活沉睡的文化基因,在虛擬與現(xiàn)實的交疊處培育新的文學土壤,這個“根”的價值厚度,我們該如何評判?
相聚汨羅江畔的那些作家與學者們,不斷挖掘楚文化的力量,這就是當代創(chuàng)作者在數(shù)字“霓虹燈影”之外,尋找人性的微光。這個時代的“尋根文學”,已升華為對人類主體性的捍衛(wèi)。
在算法主宰的時代,“尋根”已非簡單的懷舊,而是一場主動的文化溯洄與精神堅守。我們需自覺回歸歷史縱深,重新打撈那些被遺忘的敘事資源——古老的神話、口耳相傳的歌謠、被湮沒的民間智慧。某種意義上說,如今的“尋根”,就是頑強守護那源于生活深處、充滿矛盾與豐饒的復雜敘事,堅守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的“不可壓縮性”。文學最珍貴的根系,應該依然深扎于人類那充滿疼痛與渴望的靈魂深處。因為哪怕能用大模型重構《紅樓夢》的人物關系圖譜,但最終打動讀者的,依然是寶黛之間、大觀園的女性之間超越理性計算的情感羈絆,是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凈”中那種生命最深處的悲涼空寂。
我想,尋根文學有了新的使命:它既是對抗技術異化的精神堡壘,也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文化臍帶。文學的根性,是對“不可模擬性”的執(zhí)著追求——因為人類靈魂深處的詩意,才是文明長河中永遠閃耀的星光。
責編:劉暢暢
一審:印奕帆
二審:蔣俊
三審:譚登
來源:華聲在線